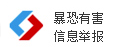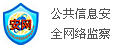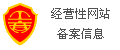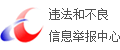故事:我是浙江的千金大小姐,3个儿子死了两个,其中有个死于偷女人内衣。 |
| 发布时间:2023-02-01 11:23 来源:未知 作者:qingtian |
|
前几天,我翻儿子的课外书,看见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
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……仿佛随口就能背出来。
老公夸我厉害,学生时代的东西还能背得一字不差。有时候,越是儿时的记忆,越是一生的陪伴。
七八岁的样子,小小的城市里,飘着热闹的蝉鸣。云朵像白色的鲸鱼,浮游在湛蓝的天空里。
奶奶的头发还是花白的,一丝不苟地拢在脑后,挽成髻。
她不同于别的农村妇女,自幼饱读诗书。我和她在一起的那几年,她教会我背古诗,诵古文。
有时我会和她耍赖说,奶奶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呀?我不懂啊。
她也不会生气,只会耐心地说,倩倩还小,不用急着明白。时间还长着呢。
祖籍浙江,外曾祖父算是红顶商人,身带官职,又经营有道。时代交替,他从浙江转来福建,依然是名门旺族。
兄长们当官的当官,开厂的开厂。而她还是个小丫头,老妈子们护前护后的小千金。
师父看了八字,摇着头,叹气说,钱我不要了,这孩子的命格我解不了。另请高明吧。
后来,他和外曾祖母说,既然这孩子未来不定,在咱们手边的日子就多宠宠吧。
到了上中学的年纪,曾祖父挑了最有名的女校让她去读。
虽说到处嚷着新时代女性要如何如何,可事实上,封建的礼法教条一样不少。
奶奶上下学,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,不是坐轿子就是坐车。
那时候的奶奶,是金丝笼里的幼鸟。外面的世界打得一塌糊涂,可她小小的天地里,锦衣玉食,歌舞升平。
她爱美,喜欢旗袍。家里有相识的宁波师傅,总能先打回上海最时髦的布料款式来。
即便是不上学的假日,她也会穿戴整齐,读一会儿书,或是坐在骑楼的窗边,吃一碗自家摇出来的冰淇淋。
吃补品的时候,还会给我奶奶分上一碗。人参炖鸡了,雪耳燕窝了……
有一次,奶奶听到送药材的伙计和老妈子闲聊,说这次送来的是血燕。
因为金丝燕的窝总是被摘走,最后累到啼血,才造出罕见精贵的血燕来。
她心地善良,心疼那些燕子小家被毁,啼血殒命。即便外曾祖母送来,她也会悄悄倒掉。
直到1941年5月,国军发动大湖战役,鏖战三日,歼敌无数。
而就在这次战役中,有一个人,因为英勇善战,脱颖而出,从此一路加官进爵。
如果说奶奶是活在时代剧的光鲜小姐,爷爷就是民国纪录片里的真实难民。
爷爷一无所有,只剩命一条。他骨子里,带着股亡命的匪气,没有生死可畏惧。
1943年,我外曾祖爷在省城见到我爷爷的时候,他24岁。
那年头,官也好,商也罢,都比不过手握枪杆子的更踏实。
所有的未来都藏在红布之外,等着一个陌生男人去揭晓。
他抱住奶奶,刚想亲热,窗外几只不识趣的乌鸦忽然叫起来。
爷爷顿时来了脾气,骂道,你奶奶个腿的,扫老子的性。
到头来,还是嫁给了目不识丁的草莽汉子,纵有千般道理不如两颗枪子更有用。
他和我爷爷同是河南一起逃荒出来的朋友。两个人相扶相助,一路走到福建来。
同是打日本鬼子。只不过一个进了国军,一个加入了游击队。
秦爷爷无不羡慕,想不到一同出来,我爷爷名利双收,还抱得美人归。
爷爷大笑,说,什么名不名,利不利的,除了我这婆娘,全都分你一半。
本以为能过上太平日子,可连年内战,军阀互斗,我爷爷也搞不清为何而战。
49年前后,许多士兵来不及告别,被带去了海峡对岸。
那时候,虽然住在小城,但日子并不苦。毕竟爷爷早有准备。积蓄还是有的。奶奶的贴身老妈子也一直跟着,照顾奶奶的起居生活。
他是河南人,爱吃面食。手把手地教我奶奶包饺子,烙饼,擀面条。
新闻里也总会出现一些曾经的官太太被遗弃落拓的新闻。
奶奶问爷爷,你当初怎么没自己走呢,到那边接着当官不好吗?
我爷爷就说,我是个粗人,但不是混蛋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嫁给我,给我生儿子。我这辈子不会负你的。
嫁给爷爷这么多年,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时,奶奶心里,没有爱这个字。
而如今,粗茶淡饭,简朴布衣,忽然有了种稳妥安逸的甜。
毕竟大环境使然,挣不到什么钱。爷爷又是个仗义疏财的爷们儿,手脚太宽。
1954年,奶奶生下我二伯。57年,生下了我姑妈。62年,又生下了我爸。
凡事都要学着自己来。爷爷疼惜她娇贵,不让她做重活。
爷爷的身份,毫无疑问成了致命伤。他性子刚烈,经不起侮辱诬陷。
68年,一场重病再也没起来。弥留之际,秦爷爷来看他了。
那时候,风声正紧,多少爷爷帮过的朋友都不敢露面。只有秦爷爷有胆有义。
爷爷攥着他的手说,兄弟,我要先走了。可怜我妻儿无依无靠,带我照应照应吧。
真是风雨轮流,命运无常。爷爷戎马一生,却落得凄凉收场。
奶奶理了理鬓角的头发,温柔地说,都长这么大了,以前来我们家吃卤肉的时候,还光屁股呢。你叔不在了,怕是以后想吃也吃不上了。
奶奶站在院子里静静地看着一地狼藉,焚花散麝,无处话凄凉。
奶奶一辈子娇生惯养,哪里干过农活。一双手,白白嫩嫩,伸出来,大家都围过来瞧一瞧。
那段时间,奶奶每天带着我姑妈下地挣工分,供着二伯和我爸去读书。
奶奶说,疼也没事。等长好了,生出茧子来。以后就再也不会疼了。
其实人心这也是这样吧,伤了,好了,慢慢也就硬起来,不知疼了。
是想刁难她的吧。可我奶奶提着桶就走了。结果回来的路上,体力不支,摔倒了。左臂骨折。
我想,奶奶是哭过的吧。但是没人看见过。邻居朋友没有。
我爸,二伯,姑妈也没有。她在所有人面前,永远从容淡定。
虽然穿着一样的蓝布工装,可骨子里,永远带着从上而下的优雅与淡然。
奶奶回城,已经是77年了。那时姑姑已经嫁给了当地的农民。
秦爷爷明里暗里用了各种办法,把我大伯从东北接回来。
在秦爷爷的帮衬下,我大伯进了邻市的煤矿单位下井挖矿。我二伯和姑妈也全部进了工厂,做了城镇职工。
她说,放心吧,孩子们都有着落了。我这辈子也差不多了。等他们生儿育女,我就找你去。
不久,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,带着五色斑斓的光彩来了。
毕竟刚搬来漳州的时候,还有奶奶的老妈子,追着他喊小少爷。
奶奶能平顺的接受人生大起大落,不代表她的孩子也可以。
大伯已经奔四了,年轻的时候,在大兴安岭里吃尽苦头,如今又混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讨生活。
奶奶想不到终于熬到了光明的新时代,却仍要面对无比残酷的白发送黑发。
她经历过太多的风霜,唯一地抵御方式就吞下悲伤,活下去。
为人仗义,可做事莽撞。爷爷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人,不只胆大,还心细。
1987年,我爸都结婚了,我二伯仍然是孤家寡人。积蓄没有,能力有限。
家里人猜测,是感情上的不顺让他的心理多少有些扭曲了。
警察搜到他家的时候,竟然找到了一堆偷来的女人内衣。他就以这么不光彩的名义被抓了。
然而真正受到刺激的,不是奶奶,而是她最小的儿子,我爸。
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,品着生活里的低微艰苦,听在耳朵里的,却是大伯对往昔的怀想。
他不允许家里人去求秦爷爷帮忙。低三下四,辱没了自尊。
秦爷爷要认他做干儿子,他也不肯答应,觉得那是没骨气,攀高枝,推我姑妈去做了干女儿。
不能说,他不聪明。早早就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气息,辞职下海。
一个心里极度渴望名利与儿子的男人,没有多少女人可以受得了。
那是我一生中,最难忘的时光,得到了奶奶无尽的疼爱。
后来,我爸偷偷拿了奶奶的八字去问神婆。人家和他说,奶奶不是命薄,是命硬,克家里的男人。
我爸想起了爷爷,大伯,二伯,再联想到自己,他就怕了。
有时想想可笑,一家子的兴衰生死,竟全都怨怪在一个女人出生的日子上。
我猜,奶奶大概是知晓了,也信了。她再没有主动找过我爸。
她只是对我格外的好,她把心里对小儿子的所有的想念与深爱,都转移给了我。
她总是在院子里吸。阳光金红的傍晚,倦鸟飞过屋顶,流霞缀满金边。
而我妈回来了。她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家庭,愿意带我走。
临走那天,她一直在轻轻抚摸我的脸,眼睛里像盛着一碗透明纯净的水。
后来的几年,都是姑妈在陪着她。那时候,姑妈下岗了,在市里做了家政。
曾几何时,她也是被人伺候的小小千金,如今女儿却要落得要替人服务了。
接到姑妈的电话,我飞快地赶回去。奶奶躺在床上,像一叶年久失修的小舟,快要沉没了。
她见到我的时候,眼睛里瞬间有了光,却又悄然黯淡了。
这些年,我读了大学,结婚生子,做了妈妈,越发体会到奶奶的凄苦。
她从小被教育做一个温柔贤德的女人,她少女时期应该也有过很多美好的期许。
可她改变不了什么,多舛的人生,注定是首时代的悲歌。
有时觉得,奶奶一生都是坐在床上的那个新嫁娘,永远等待着命运去揭开那块蒙在头上的红盖头。
唯一能做的,就是用一生的优雅,从容地审视着人间潮起潮落的欢喜与悲凉。
作者 | 猪小浅,一个只写真实故事的公众号。在这里,你将看到百态人生。读猪小浅,相信爱。后台回复目录,可阅读所有故事。公众号:猪小浅 ( ID:zhuxiaoqian0214)
|
|
|
|


 主页 > 社会话题 >
主页 > 社会话题 >